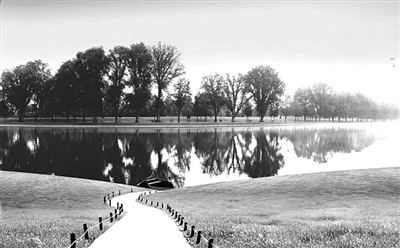我们(62-68岁)这拨人,出生在解放前后,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称之为“老三届”。这拨人吃了不少苦。历经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解放初期的事虽印象不深但有记忆,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正趋生长发育期,别说穿戴,那饥饿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
我出生贫农,姐妹兄弟八人(二姐妹自小被领养),本人排行老五。我家在农村属尽农户,幸在父亲还有门裁缝手艺,农闲时上门为乡邻做衣服,有些额外收入。也真是这样的机会,让我乘上了父亲干活的顺风车被东家叫去吃晚饭,俗称“倚轧车”。那时我十岁左右,比我大的哥哥去不成,比我小的妹妹去还怕羞,我就成了唯一的合适人选,跟着父亲吃起了百家饭。如此口福让兄妹们羡慕又无奈。纯农户的生活来源除了粮食生产队分的,日常零用钱主要以养猪蓄钱来维持。万一猪还未到出售时,家里无钱又急需用(走亲访友、看病等)怎么办?去刚出售猪的邻居家借钱调头寸(一般3-5元)。等到自己卖完猪回来当晚还剩下一半左右(20-30元),另一半已还债或被借。当时的农村就如此亲帮亲邻帮邻地搀扶着。等父亲卖猪回来的唯一心愿就是有几只好吃的菜。如猪血、内脏、再好一点的是猪头肉再带点海鲜……这就是父亲对全家的酬劳。平时家禽的蛋也不是随便吃的,更别说杀鸡宰羊。母亲总是劝说:平时自己省一点,等亲眷来了一起吃。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要吃好一点的菜就是一等猪出栏(卖猪)二等亲眷来。我有三个姐姐,最有盼头的是希望姐姐姐夫来,她们来了母亲总会烧二三只好菜,如花生炒蛋,红烧鲜鱼干(平时自己捉的晒干),咸菜粉丝汤……并在开饭前母亲常叮嘱“小囡吃饭筷头细一点(看菜吃饭)。母亲也有为难库存缺货的时候,就凭手艺,擀制面条割些韭菜做汤面加上荷包蛋来招待客人。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那就更不用说了。一是没钱化二是价格高,一个鸡蛋要1元多,想吃一顿鱼肉就成了奢望。连炒菜的油是用棉花絮蘸了油或用猪油在锅底揩一遍就是。园地里的菜不够吃就把山芋藤,蒲公英、连胡白萝卜的叶子一起吃。十三四岁正是小学四五年级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没有好菜不算连饭也吃不饱。就算一时吃饱了也只是撑饱的,吃的是籼米和炒焦米的饭,这饭软绵绵的涨性极好,吃在嘴里不用嚼二三下就下肚,一二个小时就饿了,怎么办?口袋里藏着喂猪的饲料,俗称"花肉饼",它是棉花籽榨油后剩下的壳再制成的一种片状物。有的同学还带着山芋干等,这就成了同学间交换分享舌尖上的幸福。
中学后期,自然灾害已过,粮食有了缓解。我还有二个幼小的妹妹,父母熬过了艰难岁月但健康严重透支体弱多病,经济上成了困难户。当时学校有3元、5元两档的助学金。我凭生产队和大队的证明,本人的申请,学校给了5元的补助。我每月留1元买学习用品等,其余交父母。父母又为我加工磨制麦粉熟猪油带回学校充当点心和营养品。清苦的学校生活一块乳腐分四次,一个咸蛋分六次。那时住校师生自带粮食,一天三餐用饭盒自己淘米加水。这样难免会有米粒冲入水槽流进下水道。当时我们班团支部成立了学雷锋小组,在水槽出水的地方放个大水桶,每餐后将水桶里的米用淘箩清洗干净晾晒,每天可回收一二斤米(住校师生300多)。学校食堂就用这些米不定期为师生们免费提供油汆粢饭糕。
天方夜谭式的经历讲给小辈们听,他们总是连连追问: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样?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尊警钟。我留下此言仅作历史片段的回顾,留给小辈们若干年以后再看,又将是如何的感受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