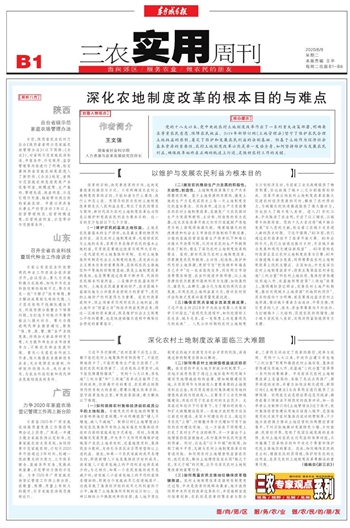作者简介
王文强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人力资源与改革发展研究所所长
[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明确要求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坚守了保护农民合理土地权益的原则,奠定了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的法制基础。但基于土地作为经济社会基本资源的重要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是牵一发动全身,如何坚持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确保改革始终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关键。
以维护与发展农民利益为根本目的
改革的目的,决定着改革的方向,也决定着改革的路径与方式。只有明确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才能知道为什么要改、改什么和怎么改。党领导的历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顺应了农民的需求与期待,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必然是以维护和发展农民利益为根本目的。这一目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农民的基本土地权益。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最主要的物质利益所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首要任务是维护农民的基本土地权益,实质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两大目的。一是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底色,是完成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是体现农民主体地位和平等地权的制度基础,既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也是需要通过改革不断夯实、巩固的农民根本利益所在。二是维护农民基本财产权利。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在当前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背景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显得尤为重要。在农村改革进程中,防止侵害并实现好农民土地权益,将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来,将这一沉睡的资本激活,既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公平性的需要,也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二)激发农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土地制度改革属于生产关系调整的范畴。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激发土地的生产力是我国历史上每一次土地制度变迁的基本要求。实践表明,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激发广大农民推动生产力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有力武器,这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分散的家庭经营面临着生产效率低下和难以对接大市场等问题,从而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了制约,催生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需求。显然,新时代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要激发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护和利用好土地资源,更好守住“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一农业底线任务,同时顺应市场消费需求转型、农业科技进步新形势,以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为支撑,加快集约化、绿色化、品牌化、融合化为取向的现代农业发展,实现农民土地利益最大化,推动农村经济由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三)确保农民共享城乡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在主持2018年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土地制度与计划经济互动,为国家工业化战略提供了物质积累,但也助推了城乡二元分割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极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取消了农业税,开启了以工辅农、以城带乡的新局面。党的十九大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强调,“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40年前的农村改革正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引擎,40年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同样需要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找到支撑点。正因如此,中央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将焦点集聚在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和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上,强调确权登记颁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推动实现城乡土地资源“同地同权同价”。其目的指向十分明确,就是要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吸引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向乡村流动,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面临三大难题
习近平多次强调,“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党的十八大以来,承包地“三权分置”和“三块地”改革试点取得了扎实的成效,但距离中央的要求、农民群众的期待仍然有较大的差距,需要从遵从改革目的、坚守改革底线出发,审视改革困境,着力解决以下难题。
(一)如何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平的土地权益。为避免农村承包地的频繁变动影响耕地经营规模,中央明确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同时,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中央多个文件均明确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据此,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的成员是增长的,即使新增人口也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家庭人口在承包地上的平均权益也将是减少的;与之相应,如果一个农民家庭的成员是减少的,该家庭人口在承包地上的平均权益将是增加的,即使这个家庭成员已经进城落户。这就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权益的不公平,偏离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设计初心。这种以牺牲公平换取效率的安排,在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有演变为社会矛盾的风险,亟待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加以解决。
(二)如何将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给农民。在当前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制度下,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通过土地征收和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增加城镇建设用地,从而获得作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其实质是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纳为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工业化和城镇建设,而返还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很少。尤其在近年经济下行背景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扩大城镇建设投资,一些地方政府想方设法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名义,通过引导农民“上楼”、村镇撤并等方式增加可用于挂钩的农村建设用地。这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打乱了农村生产生活的秩序,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增值的收益被抽走,农村集体和农民利益受到损害。同时,这也是“以乡补城”的延续,加剧了城乡矛盾,无疑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的背道而驰。如何将农村土地增值收益留在农村、返还农民,解决土地增值收益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问题,应作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
(三)如何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保改革稳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央是改革的战略决策者,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所定的改革边界执行,并因地制宜进行探索创新,农民则是改革的需求者与配合者,三者的互动决定了改革的路径、效率与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建立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和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的决策部署。中央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上是谨慎的,采取了先试点再推广、循序渐进的安排,并着力加快法制化进程,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为改革稳妥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现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者,都存在着只顾放活不顾稳定的改革冲动,如一些学者认为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过于保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该进入城市,宅基地使用权应放开在村集体内流动的管制等;不少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土地经营权向规模经营者集中,不切实际地推动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忽视了我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农村土地对农民长远利益的保障功能,从而偏离了改革的目的和中央关于尊重和保护农民主体地位的要求。因此,如何确保农民的自主权,增强农民的获得感,保护好农民的长远利益,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摘编自《新三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