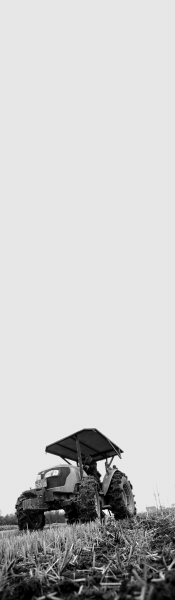本版文字统筹:王平 摄影:杨清悦
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巨变
平等保护“经营主体”
目前,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4.6亿亩。2.3亿农户中约30%的农户已流转了土地,在东部发达省份这一比例更高、超过半数。这意味着农业生产者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三权分置”实现了村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既让流出土地经营权的承包农户增加财产收入,也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了规模效益。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强调,在保护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的基础上,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以流转合同取得土地经营权。
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的农业补贴改革,基本原则是“存量调整、增量倾斜”。存量指已经给到农民口袋里的钱不会减少但会优化,而增量则是向新的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引导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除了家庭农场外,“新农人”群体还有农民合作社和“公司+农户”方式的龙头企业等。这些新型主体,可能是未来中国真正的农业生产经营者。
据农业部统计,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已超350万户,经营耕地面积3.5亿多亩。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数量已经超过270万家。
与此同时,通过农业服务社会化组织的连接,即使土地不流转也能实现规模化。河南商水县许寨村农民刘国富,平时在建筑队干活,闲时也种种地。当地的天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他提供托管服务,这让他很省力省心。今年刘国富在托管“菜单式”服务中选了小麦耕种、打药、收割等服务,小麦收获后送到家,实现了他“离乡不丢地、不种有收益”的愿望。目前,这个合作社托管服务面积有12000多亩,辐射带动了周边3个乡镇3000多农户。这种方式在不改变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实现了农业规模经营,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了收入,也使合作社获得了很大收益。
在四川崇州、江苏射阳等地,一大批专业服务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服务队涌现,为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由村组统一组织破除田埂,以打桩等形式确定界址,将碎片化的农地集中起来实现有组织的连片种植,再由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推进农业生产联耕联种、联管联营。
“一种规模化是经营主体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还有一种就是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规模不断扩大。这两种方式同样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陈锡文说。
“农地入市”破冰
农村土地农民做主
重庆市大足区是全国首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区县之一。去年以来,该区已初步建立起“农地入市”的工作流程。基层反映,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获得感”,但在土地出让收入应如何分配、集体土地能否和国有土地一样抵押融资等问题上还存在疑惑。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大足区成功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7宗,面积176.8亩,成交总金额6850.25万元,平均每亩价格约38.74万元。大足区国土局副局长罗晓宏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无经验可循,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大足区对照改革试点要求,围绕产业发展和功能定位,主要开展了集中区入市和就地入市两种入市途径的探索。在邻近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景区大足石刻的宝顶镇东岳村2组,集体经济组织将原有偏远、闲置、零星分布的110.54亩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复垦后,集中到区位优势明显的公路边作为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集中入市。去年11月,3名竞买人经过11轮激烈争夺,重庆大足石刻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最终以3950万元的价格(35.73万元/亩)成功竞得40年土地使用权,用于打造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博览园。而在龙水镇保竹村,2.52亩具备开发建设基本条件且可在本村直接使用的工业用地,实行了就地入市,用于生产办公经营,解决其农村小微企业用地难、融资难问题。罗晓宏说,大足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从头到尾尊重农村土地权利人意愿,充分反映农民利益诉求,入市地块交易方式、交易规模和分配方式由村、社集体通过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进行决策,整个上市交易过程群众全程参与,做到了农村土地农民做主。
在大足的改革试点中,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的实际“出让”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成员不管有没有被占地,都能参与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因此,基层群众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认为这是一项好政策,获得感十足;乡镇和村社基层干部则认为,这项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干部虽然会辛苦不少,但非常值得;而参与的企业认为,能够“直接购买”农村土地,拓宽了企业用地途径,便于扩大经营和发展,企业非常支持。
“入市改革政策好,人民当家作主了,收益节余归集体,百姓心里好欢喜。”这是东岳村2组村民为改革写的打油诗。在东岳村,当地村民对改革试点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与满足。52岁的原4社村民龙训明兴奋地说,他家有3口人,每人分了35000元,加起来一下子就有了10万多元钱,正好可以用于自己的犬类养殖场扩大规模。年过六旬的原5社村民罗家元和老伴两人不仅一起分得了“土地出让金”45400元,由于被占了1.3亩地,两人还可以一次性获得5320元/亩的青苗费,及每年每亩按900斤稻谷市价折算的口粮钱,一直到二轮承包期末。东岳村支部书记陈行虎表示,改革让村民有了十足的获得感,农地“直接入市”比征地制度、土地流转给农村带来的收益更大,而且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在发现土地价值的同时还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不受损,一举多得。不过,陈行虎表示,对基层干部而言,引导村民参与“农地入市”改革是个“苦差事”。陈行虎说,一下子分这么多钱,在农村错综复杂的关系下,确实对基层村社干部是一大考验。2组队长王建国说,为了分配方案,开了不知道多少次村民大会,经常喉咙痛得话都说不出来,但为了群众利益,再苦也得坚持。
作为第一个“购买”农地的重庆大足石刻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投融资部经理唐丽表示,企业非常支持国家这项改革试点。唐丽说,购买的这块地位于前往世界文化遗产、国家5A级景区大足石刻的必经之路上,是公司进行旅游配套产业建设的理想位置。“不仅地价比周边国有土地50多万一亩的价格便宜,而且没有国有土地需要计划指标那么复杂的流程,帮企业节约了不少成本和时间。”唐丽表示。
谁该分怎么分有分歧
能否抵押融资有担忧
相关调研中发现,由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尚属新生事物,虽然国家在试点区县暂停实施部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将在2017年试点结束后对相关法律进行调整,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谁该分和怎么分的问题。
入市改革村民们都支持,但分配时“架却没少吵”,首当其冲就是谁该分、谁不该分的问题。举例说,按农村传统乡规民约,农村老百姓认为嫁出去的女儿、转户进城的“城里人”就不应参与分配,但在巨大利益面前,凡是能沾边的都想回来分,最后村里只能“人性化”对待,让其参与分配。以前文中提到的东岳村4社为例,集体成员最后认定有户口有承包地的村民可全额分配,按照每人3.5万元分配;夫妻双方有一方属本社的,其另一方(嫁出去的女儿和娶进的媳妇)按40%比例,每人分配1.4万元。
其次,集体经济组织要不要留存部分土地出让金,村民和村集体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足区国土局建设用地科科长罗登华介绍说,按试点计划,集体原则上按照不低于20%土地纯收益进行提留,但在实际操作中村民却要求一次性全部分配,不能留在村集体。罗登华表示,这样的诉求也并非没有道理。
提留部分一般用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产业,但在农村,老百姓对村干部缺乏足够的信任,村民们普遍更愿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而不是留在村集体。此外,现在的农村成员权利不明确,人口流动管理有漏洞,如果不把钱分干净,说不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要求分钱,还不如一次分了省得“夜长梦多”。
针对这些问题,相关专家表示,“农地入市”的核心是分配,建议国家层面结合户籍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农村经营体制、农村社会治理等农村综合性改革,统筹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和农村集体资产分配问题,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基层关心的另一大问题是企业拍得集体建设用地后能不能和国有建设用地一样抵押、融资。唐丽表示,国家虽已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但在使用过程中,集体土地到底能不能和国有土地完全一样,企业还是有疑惑。因此,基层建议国家授权改革试点区县暂时调整实施《担保法》有关条款,经试点证明切实可行后,及时修改《担保法》相关条款,消除金融机构顾虑,让其积极参与改革试点。
如何让家庭农场主放心经营?
上海松江区叶榭镇农民沈忠良,2007年承包了146亩土地,成为全区第一批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刚成立时,只能依靠外来农机耕作,时间不确定,价格悬殊,服务没保障,经常误了农时。沈忠良咬咬牙,买了镇上第一台大型收割机。
收割机派上了大用场。但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农机,却不是每个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都有实力买农机。沈忠良看到这里面需求很大,于是在2015年联合4户有农机的农户组建了农机互助点,与周边农场签订服务协议,实现了“农机定人,服务定户,小机家庭化,大机互助化”。而沈忠良自己种了200亩水稻,还为周边1000多亩地提供农机服务。去年他们净收入20多万元,一点不比外出打工差。
在松江,土地由村集体统一流转后,还要通过民主评定和村民代表投票同意,才能经营家庭农场,这确保了把土地交给有能力的务农人。为了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稻麦良种由区里统一供种,粮食收割、烘干、出售享受一条龙服务。松江区还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联社,提供农资配送和稻米加工服务。
为了让流出土地的农户不担心基本生活,区里每年给符合条件的60岁以上村民发放每月150元的退地养老补助金。据悉,为了让家庭农场主们安心务农,上海市正在研究家庭农场主参加城镇职业保险的政策,全市3000多户家庭农场主都将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
尽管如此,沈忠良还是有担心。“希望国家能对土地经营权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或法律保护”,他说,“只有经营权稳定了,我们才敢放心投入,才能踏踏实实搞好生产。”
农地入市须征20%-50%调节金
“今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或再转让须征收20%—50%的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调节金全额上缴试点县地方国库,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今年6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管理做出规范。以实现土地征收转用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集体之间享比例大体平衡,维护农民权益为原则,办法对调节金的概念、征收范围、使用管理、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办法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取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以及入市后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人,以出售、交换、赠与、出租、作价出资(入股)或其他视同转让等方式取得再转让收益时,向国家缴纳调节金。调节金全额上缴试点县地方国库,纳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由试点县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试点期间,省、市不参与调节金分成。调节金征收部门应定期公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交及调节金缴纳情况。
该办法适用于北京、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河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省的15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市、区),有效期至2017年12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