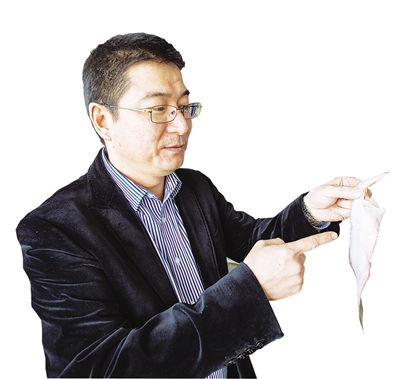“今天的海鲈鲴很新鲜,来几条清蒸一下好口伐?”熟客点完海鲜,项伟辉便让服务员带着他们亲自去挑鱼称重。从老丈人手中接管饭店十年来,凭借海鲜稳定的品质和热情的服务,已有20多年历史的天桥饭店作为当时渔业村开的第一家海鲜饭店,如今依然生意兴隆。“我主要负责饭店的管理,父亲专门打理海鲜养殖,丈母娘担任烹饪指导,老丈人则是总顾问。”和父亲、老丈人一样,项伟辉家中的男丁都曾是金山山阳镇渔业村土生土长的渔民,而如今,他们也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从曾经赖以生存的大海“上岸”成功“转型”,回忆过去,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舍。
【那些年】
一起出海捕鱼的日子
今年45岁的项伟辉是天桥饭店的老板。他告诉记者,在渔业村,他们那代“70后”都是初中一毕业就急着出海。
“要问为什么?因为当时村里没有多少好的村办企业,几个小工厂也容纳不了多少人,渔民这个身份含金量足,说到底就是赚得多。”项伟辉坦言,80年代末,一般工厂里一年做工下来也就3000多元,而出海捕鱼少说也能赚个万把块,比起其他村里农民务农,这个收入还是十分可观的,大家都愿意干。1988年,项伟辉凭借学到的一些机器保养维修技术,开始跟着父亲出海。
“出去一次就是一月半月的,留不了两天又要出门,吃住全在船上,真的十分辛苦。”回忆起那些年出海的日子,项伟辉的父亲项国余体会得更深。
和当地年轻人一样,老项21岁上船,出海打鱼,远洋近洋都跟过。“那时候村里21对船,每对船20多个人。”老项口中,出海的日子既危险又具有挑战,追着鱼汛,大批的带鱼、小黄鱼哗哗地捞上来。“跟着船老大,闻着黄鱼的气味慢慢寻找,必须十分小心,否则船就搁浅了。”老项说,有一年他们到连云港避风,因为不熟悉地形,就小心翼翼地跟着江苏的船进港,退潮的时候才发现刚刚途经的居然全是沙滩!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项伟辉跟着父亲还有兄弟上了同一条船,整整三年,老项父子仨都是在海上度过的,他们跟着船队远至韩国济州岛,也曾在十级风的甲板上拼命赶着往避风港的方向走,出海的日子,只剩母亲一人在家留守。
“钱是赚得到,但实在很累很危险。”项伟辉的老丈人陆奇龙今年71岁,记得那些出海的日子,他每天要迎接天气和海浪的挑战。从四五个人操作的“小划子”,到木帆船、机帆船,直到100吨级的大型渔船和钢质渔轮,陆奇龙也把战线延伸到了更远的海面。
“每次风浪卷起来,船都要开7—8小时才能到避风港,晚了一个小时就会很危险。”在陆奇龙他们老一代渔民的眼中,尽管充满风险,打鱼的丰厚收入仍然让人无法抗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还实行集体分配制,鱼打捞上来后统一放到运输船上,按劳分配。后来就改为自产自销承包制。
“有一年,船转弯时速度太快,一个不小心翻了船。我是从小金山游回岸的。”谈起那次“生死经历”,陆奇龙如今可以淡然一笑。黝黑的皮肤、清晰的皱纹,还是把他那些年历经风雨的沧桑明白地刻画在脸上。
【转型期】
“上岸”实属无奈
陆奇龙告诉记者,现在村里1000多人,真正的渔民只有100个出头,渔船也只剩下18艘了。村里最年轻的渔民也已年近半百,很少有年轻人再愿意出海打鱼。他们大多都到镇上、市区上班,捕鱼生活似乎离他们越来越远。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众多化工企业的兴建,大量污水流入杭州湾,再加上过度捕捞,渔业资源逐步衰竭,形成了渔船搁沙滩的状况,渔民只能告别赖以生存的大海,有的务工,有的经商。1979年,陆奇龙率先“上岸”到厂里做事,后来和太太一起经营饭店。1993年,女婿项伟辉和他父亲也都“转型”为普通村民。1996年,项伟辉在“上岸”后曾试着再次“下海”,他和朋友一起买了条船出海单船作业,一年下来赚了一万元都不到,于是彻底断了“念想”,一心一意开始饭店生意。如今,他和父亲、丈母娘一家把海鲜饭店经营得有声有色。
【好光景】
卖海鲜,口碑顶顶要紧
开饭店应该是1988年吧,当时是村里的第一家饭店。老头子那时已经“上岸”在企业里做事。政策开放了,我就琢磨着想自己创业,当时儿子反对,老伴也反对,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年个体户还是个稀奇事,我可不管他们,还是干了起来。
原来我做过企业的仓库保管员,至于烧菜的手艺都是跟外婆和太婆学的。我们渔业村里的人,一般都会烧海鲜的。我家里人特别会烧鱼,红烧的、清蒸的……我从小跟着学,现在也能烧一桌原汁原味的海鲜大餐了。
刚起家那会儿每天都起早摸黑地干。天不亮地去买菜、洗菜、切配、烹饪,我一个人全包下来。后来生意越来越好,店里规模也扩大了,从原来的老店搬到了现在这个小楼。再后来我就把手艺传给女婿,教他烧菜。
这几年,金山嘴“海鲜一条街”名气大了,客人也多。有些散客半夜一点钟会想吃夜宵,厨师下班了,我就亲自给他们烧,客人们都很感动。想想当年他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还好我坚持要做。
采访到现在,你们饿了吧,快尝尝我烧的蚕豆!你们今天是来得巧,我每隔一个礼拜去上海带孙子,一个礼拜在饭店里。
——杨婉华
打鱼风险大,收益少,渔民总归会越来越少。儿子打了几年鱼上岸了,孙辈们更是不知道也不关心曾经海洋生物带给村民们的喜与悲。采访中,年过七旬的陆奇龙和项国余流露出对过往打鱼生活的念念不忘,“游客们来到这里,逛逛老街,看看展馆,品品海鲜,多少都能了解一下渔人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更不应该忘记。毕竟这里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