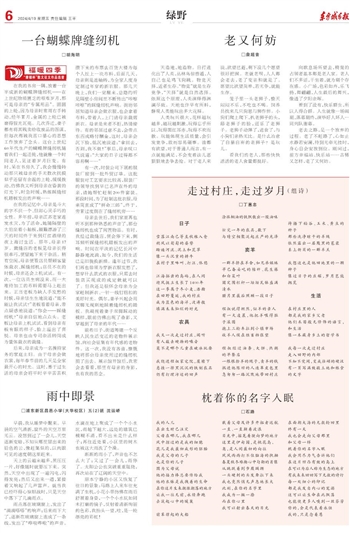□胡海明
在我的书房一隅,放着一台半成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在上世纪物质匮乏的艰难岁月,那可是母亲的“专属用品”。圆圆的上轮,因为母亲时常用右手转动,经年累月,金属的上轮已被磨得锃光瓦亮。几次乔迁,妻子都有将其贱卖给收废品的图谋,但每次都被我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放弃了念头。这台上世纪60年代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随着我们一起迁徙,他就像一个时间老人,见证着岁月巨变。有时,呆在书房久了,我会慢慢转动那只被母亲的手无数次抚摸似乎还留有余温的上轮,缓缓拨动,仿佛我又听到母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时急时缓,熟练踩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声响……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却心灵手巧的女性。多年前,母亲江苏老家连发水灾,为了活命,她随隔壁的大伯坐着小舢板,颠簸漂游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来到灯红酒绿的夜上海讨生活。那年,母亲17岁。裁缝店的老板见母亲长得很乖巧,便留她下来干杂活。稍有空闲,母亲便看店员帮顾客量体裁衣、踩缝纫机;店员不在的时候,母亲还会上机试试。有一次,一位店员生病没来,而一大堆待加工的布料需要马上赶出来。正当老板为缺人手发愁的时候,母亲怯生生地说道:“能不能让我试试?”老板看着母亲,带点疑惑地说道:“你会——踩缝纫机?”母亲自信地点点头。老板让母亲上机试试,看到母亲有板有眼的样子,脸上溢出了喜悦。母亲也由专司杂活转岗成为量体裁衣的裁缝。
后来,母亲成为一名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由于母亲会做衣裳,每年春节前的几天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光。这时,善于过生活的母亲会将平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布票去百货大楼为每个人扯上一块布料,后面几天,母亲则是连轴转,为全家人度身定制过年穿的新衣服。那几天晚上,我们一觉醒来,总隐约听见隔壁小房间里不断传出“咔嚓咔嚓”的踩缝纫机声响。街坊邻居知道母亲会做衣服,也会拿着布料,带着人,上门请母亲裁剪新衣。母亲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有的邻居过意不去,会带点东西或略付酬金,这时,母亲会沉下脸,低沉地说道:“拿回去,否则,我不做!”事后,母亲叹口气说道:“大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
有一次,时装公司下属的服装厂接到一批外贸订单。这批服装对工艺要求比较高,服装厂的领导找到早已名声在外的母亲,请她帮忙赶制200件套装。那段时间,为了赶制这批衣服,母亲简直成了“拼命三郎”,终于,劳累过度倒在了缝纫机旁……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里再也听不到那种熟悉的声音了,那台缝纫机也成了闲置物品。有时,我经过裁缝店,便会停下来,侧耳倾听踩缝纫机踏板发出的声响。时间在平淡的记忆长河中静静地流淌,如今,我们的生活已是旧貌换新颜。逢年过节,我们再也毋须为穿新衣服发愁了,想穿什么款式的衣服,只需去时装店买现成的或定做就可以了。但我还是很怀念母亲为全家赶制新衣、一针一线钉纽扣的美好时光。偶尔,妻子兴起会用双脚无规则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我凝视着妻子双脚踩动的模样,眼前仿佛出现了叠影,又穿越到了母亲的年代……
前些日子,街道筹建一个反映人民生活变迁的老物件展示馆,向社会征集有年代感的老物件。这一次,我没有吝啬,慷慨地将那台母亲使用过的缝纫机捐了出去。展示馆开馆后,我常会去看看,那里有母亲的身影,也有我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