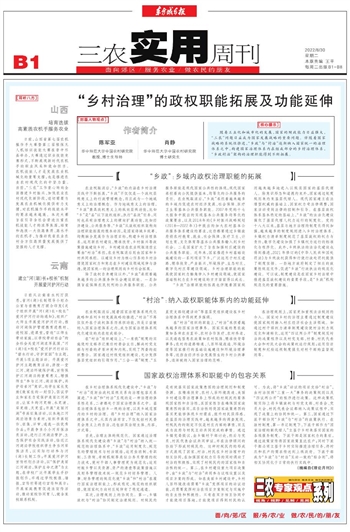[封面人物观点]
作者简介
陈军亚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肖静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博士研究生
[核心提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家的财政能力日益强大,“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系统性推进,“乡政”与“村治”逐渐纳入国家统一的治理体系之中,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政村治”架构的治理职能得到不断拓展。
“乡政”:乡域内政权治理职能的拓展
农业税取消后,“乡政”的内涵在乡村治理实践中不断拓展,“乡政”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层级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概念,而且成为一个地域意义上的治理概念。作为地域意义上的治理,“乡政”兼具政权意义上的纵向层级功能,比如“乡”是“县”以下政权组织,执行“县政”任务,同时也具有治理意义上的横向扩展功能,比如经济建设、公共服务等。“乡政”从政权组织架构向治理职能拓展的根本动因,是国家将城乡统筹、均衡融合发展作为治理目标,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运用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策措施建设乡村。乡村建设在农业税取消前主要由“村治”承担,农业税取消后则由国家和乡村共同承担。以建设乡村为核心任务的乡村治理使国家权力和意志在乡村建设领域延伸与渗透,使国家统一的治理规则向乡村社会拓展。
除了政权自身建设以外,“乡政”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职能。一是加强旨在保障农民权利的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职能是现代国家公共性的体现,现代国家承担着向公民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农业税取消后,“乡政”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乡域内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职能。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要求,以及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的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这些都要通过乡镇政府将农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输入到乡村社会。二是国家扩大了旨在加强村庄建设的公共服务职能。近年来,国家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系列项目下乡,广泛运用于村庄道路、精准扶贫、产业振兴、环境保护、生态村庄、数字化村庄等建设领域。乡村治理职能的拓展使国家权力触角伸入乡村建设领域,使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得以成长。
“乡政”治理职能的拓展也伴随着国家规则越来越多地进入以规范国家的基层代理人。除意识形态和道德约束外,国家通过制度规则来约束基层代理人。现代国家建立在法理型权威的基础上,国家权力受法律调整,国家活动受到法律的控制和引导。在基层政权体系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乡政”的法治化建设强化了基层代理人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化得到加强,越来越多的制度规则进入乡村治理体系。乡镇权力清单制度规范了基层政权的权力与责任,数字化建设加强了乡镇权力运行的标准化与程序化。此外,乡级执法的法治化建设也得到推进,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罚法》为乡级政权获得和行使行政处罚权提供了制度依据。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性规范文件,促进“乡政”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可以说,制度建设是在国家乡村治理中推进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手段,是“乡政”机构规范化的重要措施。
“村治”:纳入政权职能体系内的功能延伸
农业税取消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战略和系列乡村发展战略的推进,“村治”不再仅仅外在于政权体系而承担功能,而是日益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村治”组织建设上,“一肩挑”制度的实施使村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解决村党支部与村委的矛盾冲突和内耗,实现了两委的组织整合。国家通过村级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三会一课”制度、“五星党支部创建活动”等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得到更多强调。
在“村治”组织的职能上,“村治”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治理事务。国家实施的惠农政策如各种农业直补、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以及遴选型惠农政策如农村低保、精准扶贫等事务;农村的道路畅通、人居环境改造、环境治理等国家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事务等,这些由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乡村公共事务,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
在治理规则上,国家更加重视法治规则的介入。国家对乡村的治理主要通过制度建设使国家规则融入村庄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如通过村干部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使村治权力规范化和清晰化,运用“四议两公开”制度规范村治的决策程序以及村党支部、村委、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决策权运行规则;运用信访制度和纪检巡视制度强化对村干部的监督规则等。
国家政权治理体系和职能中的包容关系
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乡政”与“村治”逐渐由政权层级关系向治理包容关系演进。“乡政”和“村治”呈现的是一种治理的体系性关系,二者都处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基层治理体系包括乡一级的治理,以及乡域范围内的乡村的治理。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从其内涵而言,不仅包括村民委员会意义上的自治,还包括其治理主体、内容、方式等。
首先,治理主体的规范化。国家通过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将“乡政”与“村治”纳入统一规范的治理体系中。“乡政”运用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技术与村治联结,运用坐班制、专职制、工资制、考核机制等类似公务员管理的权力技术,使村干部人事管理更为规范化;运用村账乡管以及资源、资产的清查等政策措施以及财务管理技术统一规范乡村财务管理。人事、财务管理的规范化使“乡政”和“村治”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上,形成稳定、规范的组织联结,使国家权力向村庄延伸有了稳定通道。
其次,治理规则上的协同化。第一,乡镇政权与“村治”协同制定治理规则。村规民约是有效落实国家政策意图的治理规则和制度资源。在精准扶贫、农村人居环境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治理事务上形成的村规民约要体现国家性和自治性,其国家性旨在确保国家政策意图的落实,其自治性则使国家政策意图的落实更能够体现乡村需求,提升村民获得感。在基层的治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调查发现,村规民约的制定不仅是村庄内部的事情,而且成为政府与村民互动共同完成的事情。通过乡镇党委提议,由乡镇村干部讨论,然后与党员、村民代表会议共同审议,并在法律顾问的协助下形成村规民约。这种村规民约的形成方式展现了国家、村治、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相互协同,在加强国家权力引导的同时调动了村治的积极性,实现了村规民约的国家性和自治性的统一。第二,在乡村建设重大项目决策中,由“乡政”与“村治”共同参与议程设置以及项目方案的形成。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乡村人居环境改造需要“乡政”发挥项目的动议功能,还需要发挥村治在项目方案制定与实施中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只有在双方相互协同中才能使项目落地,才能使项目得到村民的认可。为此,将“乡政”动议的项目交给“村治”,由村治按照“三重一大”事务的决策规则以及“四议两公开”的程序进行决策。这种决策机制实际上将乡镇政权与村党支部、村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都纳入决策议程中,实现了决策上的协同和统一。第三,国家通过下派干部协同“乡政”与“村治”的政策执行。在驻村制度、第一书记制度下,下派干部作为“国家治理的新代理人”立基于乡村来落实国家的各项服务制度。下派干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通过政策宣传将国家政策直达农户;同时下派干部必须立基于乡村实际推进治理任务,将村庄和农户的需求传达到上级政府。下派干部成为“乡政”与“村治”互动一致的“粘合剂”,将相互协同化于日常的执行实践中。
(摘编自《理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