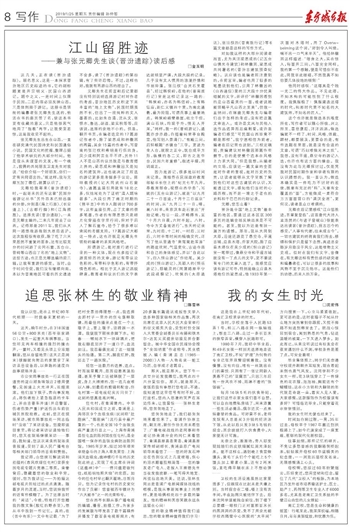这几天,正在读《晋汾遗踪》。顾名思义,这是一本探求晋汾地区历史踪迹的书,它的副标题更是开宗明义:民国山西游记。题中之义,一是时间上仅限于民国,二是内容必须反映山西,三是体例限于游记。这册书是领衔的编纂者张元卿先生送的,他还在书的扉页签了名,使这本书更有收藏的意义,只是他很客气地用了“指教”两字,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收受不起的。
张元卿先生出生在山西,一直在研究清代民国诗史和民国通俗小说。民国文化的挖掘、整理占据了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时间。他是我从未谋面的文友,有一个晚上,我俩的共同朋友卫龙先生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你们一定有共同语言的。”就这样,我与元卿互加了微信,就算认识了。
元卿给我寄来《晋汾遗踪》时,一起寄来的还有这套“民国分省游记丛书”另外四本已经出版的分册,分别是《海上行旅》、《长安道上》、《古都行脚》和《江海揽胜》。选择先读《晋汾遗踪》,一来是元卿主编的,二来几年前去了山西。记得那是2011年,我们从大同一路悠哉游哉到太原后返沪。这次旅程很有收获,除了吃了六天里居然不重复的面条,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游了云冈石窟、五台山、晋祠等山西出了名的“地上文物”,这些古迹,也正是元卿选编的前三辑,让我有重游的感觉。当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继续向南,本以为晋南地区可看的历史遗迹不会多,读了《晋汾遗踪》的第四辑,有了些许后悔。不过,这样也好,我就有再游山西的理由了。
元卿先生在前言和后记里都没有特别说明选择游记时对作者的考虑,晋汾地区历史积淀下来丰富的“地上文物”,民国时期虽然不长,但出了一批纯粹的文人墨客的,比如朱自清、沈从文、张恨水、鲁迅、胡适、梁实秋等等,应该说,选择的余地不小的。但是,翻开书页,在编者选定的17篇游记作者中,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其余15篇的作者中,写晋南的张珪权和希明是行伍出身,吴少成和阿芸生平不详,另外11人不是山西的议员就是与教育搭上界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是知名的建筑师,这也就决定了所选的游记更多是考据多于议论。陈垣教授的《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通篇直接引用就有18处之多,仅结尾处为了证明“清人题咏甚多”,大段引用了雍正时期的《朔平志》中的9人题词计700多字,这些直接引用,占了文章的很多笔墨,作者的有限思想只是碎片化穿插在字里行间,但对于后人了解石窟寺,给予了很多难以查阅的考据支持。17篇游记大都这一特点,这也许就是元卿先生领衔的编者的求实风格吧。
所谓游记,是对旅行进行记录的一种文体,现在也多指记录游览经历的文章,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有带科学色彩的,有带抒情色彩的。相比于文人游记洒脱肆意,教育者和议员们的文字表达就明显严谨,大段大段的记录,几乎没有文人惯用的浪漫抒情和华丽辞藻。张珪权“由灵石至霍县”,经过韩侯岭,在他的《晋南旅行记》里是这样记录这一路的:“韩侯岭,亦名为韩信岭,上有韩信庙,距仁义镇四十里,为南北通衢,最为险阻,可谓兵事上最要地点。韩侯岭峭壁悬崖,屹立千仞,满山石块,均现于外,惜无人开采。”同样,我一的《晋祠游记》,通篇亦步亦趋,白描着祠里亭台殿堂,他写到入景清门,“有殿三间,后轩额题‘水镜台’三字。更进为金人台,就院之正中,筑台成平方形,纵横约各二丈,即古之莲华台,民国六年重修”,叙述平缓,用词端正。
因为是游记,很多是以时间来记录。蒋维乔在民国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任上的“纪元七年九月,奉教育部命,视察山西学务”,写就的《五台山游记》,就是“以九月二十一日首途,十月十三日返京”的时间,从“九月二十一日,晴。晨八时半,乘京汉车赴石家庄”开始记载,每日一段,详略得当,至“十月六日晨,六时半起。八时,寺中方丈备斋送行”,当天的记录里,九时后、十二时、一时后、三时后、六时半等时间的精确交代,详写了他从显通寺“乘驾窝赴浑源”的路途坎坷、气温变化、古迹寺庙和自己的身体感觉,并以“自此以下,归入恒山游记”作结尾。吴少成的《恒山游记》、关颖人的《恒岳游记》、邸毓灵的《同蒲路原平宁武段视察记》、坎侯的《太原通讯》、张珪权的《晋南旅行记》等6篇文章都是这样的写作方式。
对如我这样的大部分阅读者而言,尤为关注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和林徽因、梁思成共同署名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这应该也是编者所注意到的,在前言里,编者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说到他们,引用了林徽因的《山西通信》里的三大段十分优美细腻的文字,并评价“林徽因看到的是山西最美的一面,或者说她能领略平凡山西之至美”,但我一直纳闷,在琢磨元卿先生与编者们出于怎样的考虑,没有把这篇文章选入。或许是文风与其他入选作品迥异而忍痛割爱,或许是编者们感觉“可民国山西毕竟不都是那样”,我宁愿相信为前者。编者在后记里也说到,“三校定稿前,责编建议对林徽因那篇作些删节,目的是使整个选本在风格上力求大同。”但是我想,从编者的立场,应该还一篇文章的全面是对作者的重视,是对历史的负责,让读者能够从文字里既了解到他们对这些古建筑的认识,又能透过文字,感知他们当时的心路历程,而不是一堆之乎者也的史料和干巴巴的行踪记录。
元卿,您怎么看?
晋汾是中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地区,要通过这本区区300多页的选编全部反映出来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以为还是有挂一漏万的遗憾。那年,我从大同到太原,沿途还游览了悬空寺、平遥古城、应县木塔、乔家大院,除了应县木塔仅在吴少成的《恒山游记》里一笔带过,像悬空寺和平遥古城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文字,更不要说有专门的文章入选了。我感觉应该有游记可寻,特别是确立应县木塔地位的梁思成,他1933年第一次面对木塔时,用了Overwbelmlng这个词,“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他给林徽因这样描述:“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他同时感叹:“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这个也许就是做选本的难度所在,写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兴之所至、喜悲褒贬、洋洋洒洒,做选编就不一样了,时间、风格、体裁、题材,都要顾及,更要命的是,有些选题在里面,就是没有合适的文章,可谓“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我想,没有平遥、悬空寺的游记入选,也许也有这方面的缘由。我没有为此与元卿探讨过,仅是凭我对民国时期作家和学者有限的认识臆想的。我一直认为,做选本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既要有充足的“料”,又要有全覆盖的“面”,方能做成一桌符合方方面面胃口的“满汉全席”,更何况,读者是众口难调的。
元卿在后记里感叹“江山留胜迹,吾辈复登临”,这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很能表达出读罢《晋汾遗踪》、抚古思今的感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切古建筑的终将离我们而去,修缮和保护只是留下念想,真迹总会随岁月隐没于风尘,这是唯物主义史观。但好在我们有文字、音像在,有元卿这样有责任感的研究者和编纂者在,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和风物不至于沉沦殆尽。这是他们的功德,后来人的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