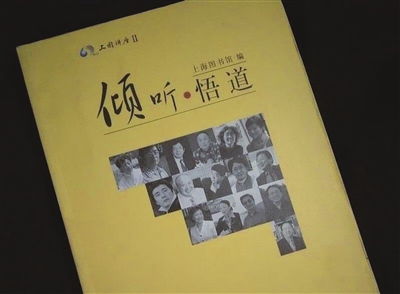口述:曾闻喜 文字:刘千荣
情事
倾诉与聆听,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请勿对号入座。(图文无关)
初中毕业的我来上海后,为了增加学识,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除了参加自学考试,报名到夜校听课外,就是到图书馆特别是到上海图书馆(下文简称“上图”),听各位名人大家的讲座,这让我受益终生。
◆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上图听讲座的陈年旧事。那是1998年的盛夏,上海少雨高温,八月底的天气预报都接近或达到高温40度。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讲座预告,说是著名作家叶辛老师在上图开展讲座。在老家我看过电视剧《蹉跎岁月》,来上海拜读过叶辛老师的长篇小说《孽债》,也看过电视剧《孽债》,当然由于受条件限制,我只是在有电视的老乡家中蹭看过几集。对叶辛老师特别崇拜,当知道到上图有可以见到真人的机会,我当然不愿失之交臂。
在无比期待中,终于等来了叶辛老师开讲的那天。我当时在天山路附近的一家仓库当保安,吃住都在仓库里,讲座那天我正好轮休。那时我刚来上海三年,只是对仓库周边道路很熟悉,但从未到过淮海路。我通过查地图,找到了上图的位置,发现离我其实不算太远。本想骑我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老爷车过去,推出来才发现内胎破了,想去补胎怕时间来不及。加之那天四十度的高温,我放弃骑车的计划,准备乘公交过去。
我顺着天山路走到中山西路,没有找到我要乘的公交。凭着查地图时留下的记忆,走到了淮海西路,在一个公交站牌上看到我可以乘坐的公交车,一看也就两站路就能到上图。站在站牌下等车酷热难当,走的时候还不觉得,一停下来立刻汗流浃背。
放眼望去也不知道那辆公交啥时候能到,我一咬牙,顺着公路打算步行走到上图。好在一路直走,不用拐弯。在滚滚热浪中,我终于到了上图,仰头看见眼前矗立的大楼,我得承认这是我从小长这么大看到最为壮观的图书馆。在此之前,我只是进过我就读的中学图书馆。
跟着人流队伍走,举办讲座的楼层倒是不难找。记得座位排序是前低后高,我去得晚,只能坐后边靠墙的位置。这样居高临下看居中的叶辛老师和工作人员,虽说离得有点远,也能看得很清楚。
叶辛老师回顾了他由知青到作家的成长经历,讲述了他的创作历程,最后回答现场听众与读者的提问。有一位家长问他上中学的孩子喜欢文学,要不要让他写下去。叶辛老师回答得特别干脆:那就写呗。我不知道那位家长是否听了叶辛老师的话,我是记住了这句话,无论打工路上遇到逆境还是顺境,喜欢文学的我都在坚持写写画画,一直写到如今。
听完讲座,我依然是走着回去的。虽说太阳已经西斜,天气仍然很热。第一次到上图听讲座,除了记住那天的高温,也记住了叶辛老师的博学与风趣,还记住了上海图书馆的高端大气。原来这座城市还有这么一个可供学习和增加知识的地方。日后,只要我有空,上图有讲座,我都尽量前往听讲。
◆看到马伯庸将在上图举办讲座的预告信息,就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眼熟,一时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看头衔是“著名作家”,心里暗暗称奇,既然“著名”,我咋就想不起来他是谁呢?那么他的代表作品又是什么呢?当我走进上图领到入场券看到背面的嘉宾介绍,终于看到马伯庸的“先进事迹”,在罗列的作品中有一部《长安十二时辰》,一下子想起来那部由雷佳音主演,曾经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原来是这部电视剧的原作者人称“亲王”的马伯庸,还真无愧于“著名作家”称号。想来不是人家不著名,而是我过于孤陋寡闻了。
马伯庸身着一袭黑衣,戴眼镜,有点学究气。立于讲台中央手持话筒开口声明他不说他最近的新作,避免让人觉得他在带货。然后说感谢这么多听众、读者来听他的讲座,随后打趣都没有男(女)朋友的是吧?接着说他还没有女朋友时和上图有缘,那时他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书,经常来上图。有次查完资料,是步行回到学校的,走了两三个小时。听闻此言,立刻惺惺相惜起来,这种“傻事”当年我听叶辛老师的讲座也干过。
马伯庸普通话标准,话锋犀利却不失幽默,自称做销售不会喝酒,做市场不会说话。但公文写得好,擅长作PPT,帮公司的各级领导写讲话稿。他是从公文写作与采访说起,慢慢过渡到他演讲的主题《跟曾巩学做事》。全程都在分析介绍曾巩的一篇文章《越州赵公救灾记》,说这文章更像一篇说明文,非常具有逻辑性。得出的结论:这篇文章更像古代版的PPT……真正精彩的还是马伯庸与现场读者的互动提问,在回答读者的提问时马伯庸可谓旁征博引,用极为生动传神的语言阐明了他的读书方法,写作观点,做人原则,还是非常自然提到他的新书《显微镜下的大明》。说是不带货,还是带货了,只是马伯庸带得高明,让人感觉不到他是在为自己打广告。
◆在上图所听的讲座里,开讲人以作家居多,其中也有节目主持人,2017年年末,我在上图就听到东方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叶沙的讲座。
我初到上海当保安三班倒,上夜班陪伴我的只有一台袖珍收音机,我和我很多同事上夜班寂寞无聊听得最多的是东方广播电台的“相伴到黎明”节目。在该节目的众多主持人里,我比较喜欢叶沙的清新和睿智,同时我发现她主持的节目不都是情感热线,而是节目开始定下一个主题供听众打进电话来讨论,这个需要广博的知识、雄辩的思维、良好的口才和快速的反应能力,叶沙把她的这方面专长在节目里可谓发挥到了极致。
也许是叶沙的节目主持得太成功了,“相伴到黎明”节目居然让她在周末开出了一档专题节目“子夜书社”,这对于喜欢读书的我来说算是觅到知音了。“相伴到黎明”里的其他节目我可以不听,但每周日的“子夜书社”我是必听的。有一次,我听到节目讨论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忍不住打了热线电话,接通后导播让等她电话通知。
在忐忑和兴奋中等来了通知电话,恰好领导过来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我在做和工作无关的事情,轻则罚款,重则除名。如惊弓之鸟的我没来得及向导播做任何解释,忙匆匆挂断电话,非常无奈放弃那次好不容易打通的热线电话,错失了一次展示自己喜读书、爱好文学的良机,同时更对节目的导播和主持人叶沙充满歉意。
后来,我更换职业不再上夜班了,因白天工作忙碌而疲惫不堪的我不再坚持收听零点以后的任何广播节目。再后来连自己的袖珍收音机都找不到了。但还是会常常想起刚来上海上夜班收听广播节目的深夜时光,“相伴到黎明”节目的开始曲时常会在耳畔回响,怀念在“子夜书社”节目里听到介绍后,买来或是借来阅读过的许多好书的日子。
怎么也没想到,十几年后我会在上图再度听到叶沙清脆悦耳的声音,听她本人在现场回顾她做电台主持人的苦辣酸甜。那天我用手机拍了叶沙讲座时的照片,发到朋友圈。一位同样是叶沙听众粉丝的朋友,说我拍得不够清晰。我很委屈地回复那张叶沙为读者签名的照片就很清楚。
◆在上图听过的讲座里也有教授们的开讲。我曾有幸聆听那些年如日中天的易中天教授在上图的讲座,一如他在央视“百家讲坛”里“品三国”时的幽默。他自嘲他最大的特点是善变,因为他姓易,易就有变换的意思。还有,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出题人,听他在上图说王摩诘,介绍白乐天,让我产生了参加诗词大会的奢望。其中叶扬教授的讲座带给我非常深的感触,启发我写文回忆。
叶扬教授在上图,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比中国大文豪苏东坡和爱尔兰大诗人叶芝在诗与画方面的造诣。听叶扬教授的讲座,发现他提到古人喜欢呼其字或者是号,绝不提名。他主讲的是苏轼,但只喊苏东坡,说到李白,要么叫李太白,要么叫李青莲;说到杜甫,要么叫杜子美、杜少陵,要么叫杜工部,就是不喊杜甫……如是喊古人也就罢了,说到现代文学家也是,他说到钱钟书,只说钱默存。大概叶扬教授也发现台下的听者一脸茫然,才解释道就是钱钟书。
我感觉这位叶教授真有意思,说他卖弄学问吧,感觉真没必要,引经据典顺手拈来,纵论中西文化字字珠玑,还在意用这点雕虫小技来炫耀其知识渊博?终于叶教授在提及王维,称其王摩诘时补充解释了一下,说这是对古圣先贤最起码的尊重——称其字和号,不能直呼其名。叶教授说早年他在家中读书,如果是他父亲,听到小辈中有人直呼李白、杜甫之名,马上就会勃然变色,训斥道“李白、杜甫那是好随便叫的?要敬畏先贤,要呼其字”。台下的我终于释然,叶教授如此喊人的字,原来是受良好的家学家风影响,既感到新鲜也非常敬佩!
叶教授介绍完了他的父亲和家学,没忘记呼吁要培养今人养成敬畏先贤的风气,不能直呼古圣先贤之名,这种习惯应该从大中小学生开始抓起,特别是语文老师要以身作则。勿以善小而不为,叶教授呼吁敬畏先贤从称呼古人的字、号这样的小事做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深以为然,后来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说话,我都注意说古人的字,而不是直呼其名,以示尊重。
从去上图听讲座以来,我还先后听过企业家王石、导演江海洋、歌唱家杨学进、二胡演奏家马晓辉、主持人骆新等名家的讲座,特别是有幸听到著名作家王蒙、苏童、严歌苓等大咖来上图的讲座。他们的学识令人高山仰止,他们的创作经历给我鞭策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