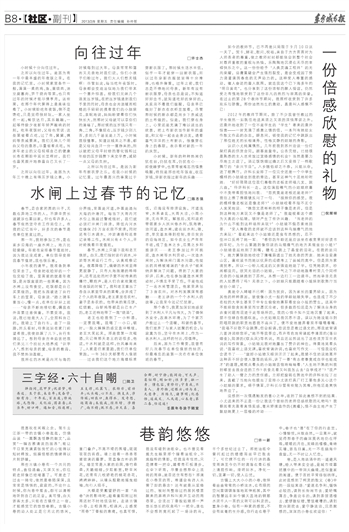我喜欢在闲暇之余,驾车去江浙一带的古镇小巷逛逛,仿佛品读“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品赏“一幅古雅清淡的图画”;能让平日里充满紧张匆忙的心弦得以短时释放,烦躁悒郁的情绪得以片刻舒缓。
那些古镇小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曲径通幽,又深又长,你往前走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且常常是悄悄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候,你向巷中踅去,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真可惜,白天游客太多,只能在古镇住上一宿,才能感觉它的悠悠巷韵。古镇小巷的动人处正是它无比的悠闲。重门叠户,不高不矮的围墙,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苍翠欲滴的藤萝,简直像古朴的屏风。墙里常是人家的后园,修竹森森,天籁细细,夕阳影里,野草闲花,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娉娉婷婷,从墙头殷勤地摇曳细袖,向行人招手。
大概是受戴望舒的一首“雨巷”诗的影响吧,趁着重阳刚过秋雨还时不时地低语时,走进古镇小巷,去相遇雨,相遇风,去感受“雨巷”丁香般的意境。也真可惜,我没有碰到油纸伞,也不曾见着戴先生眼里那个撑着油纸伞、不施脂粉的倩影。但我没有怅然,只是撑着一把伞,踏着青石板漫步,在伞下听雨,尽量去想那伞上流转的雨珠,是否还含有愁怨?那滴在小巷里的雨,难道会有诗人未曾了却的悬念?还有就是从装修过的、被时尚整容过的居民楼里醒来的麻将声和叫卖声互动的雨巷里,会流出丁香般姑娘那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吗?一把伞,谁也不会想到竟托起了一场诗的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把油纸伞曾托起过的缕缕雨丝早已散去了,可它撑不住的一行行诗的晶莹雨珠至今仍不时滴落在青石板上清脆作响,澄明如水,净化一切,笼罩一切,使人忘忧。
古镇上大大小小的小巷,依伴着曲曲弯弯的小桥流水,在有限的空间里错错落落地延伸拓展,其中的智慧远非如今铺天盖地的钢筋水泥千人一面的文明可以料定的。置身小巷,似有一种家的感觉,不会有丝毫的生分感。你行走在巷子中,巷子也“潜”在了你的行走里,心情愉悦,兴致盎然。一旦离开,就觉得那巷子的幽深莫名地仍在呼唤,暖暖的月色、发暗的楼檐、青砖瓦墙、游鸟归巢,无一不在脑海中盘旋,无一不时让人忆恋。
巷,是人海汹涌中的一道避风塘,给人带来安全感,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胜似皇家的阁道,便于百姓平常徘徊徜徉。此时我想到了柯灵的散文《巷》中的一段结束语:“爱逐名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镗、管弦嗷嘈的,请到歌台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