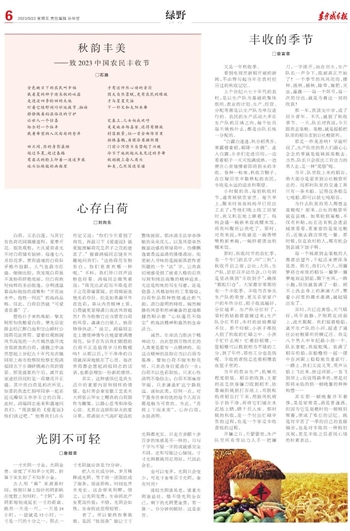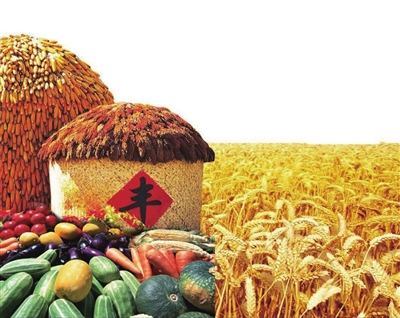□俞富章
又是一年秋收季。
看到电视里新稻开割的新闻,不由得勾起当年在农村经历过的秋收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农业的计划、生产、经营、分配等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的。农民的生产活动大多在生产队的区域之内,每个社员每天做些什么,都是由队长统一分配的。
“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寒露楼青稻,霜降一齐倒”。进入白露,乡亲们走进田间,一边看着稻子一天天饱满成熟,一边便在心里憧憬着即将到来的丰收。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庄稼田里辛勤耕耘的农民,丰收是永远的追求和期望。
小时候的我,每到秋收时节,通常被锁在家里。每天早上,醒来时爸爸妈妈早已经出工去了;等他们晚上收工回家时,我又趴在地上睡着了。妈妈会盛一碗新米饭或糯米饭,将我叫醒后让我吃了。那时,对我来说,丰收就是一碗香喷喷的新米碗,一碗拌着猪油的糯米饭。
那时,秋收时节的农忙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三秋”;秋收开启之前,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会,口号则是坚决做到“丰收到手”,确保“颗粒归仓”。大家都非常期待有一个丰收季。丰收与否事关生产队的荣誉,更关系家家户户的年终分红,稻子收成越好,分红越多。生产队分红好了,邻村的姑娘愿意嫁过来;生产队分红不好,本村的姑娘都留不住。那个时候,小孩子都投入到了秋收的忙碌之中。小孩子忙什么呢?忙着拾稻穗,一篮稻穗可以换到相当不错的工分,到了年终,那些工分也是钱呢。丰收的喜悦是连着稻穗装在篮子里的。
当年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低。稻谷的收获,主要的还是依靠镰刀收割稻禾,依靠扁担挑到打谷场上,用脱粒机将稻谷打下来,用鼓风机将谷子扬干净,再将它们铺在水泥场上晒,晒干后入库。那时候的秋收,是一个付出忙碌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享受丰收喜悦的过程。
开镰之日,天蒙蒙亮,生产队里所有劳动力人手一把镰刀,一字排开,站在田头,生产队长一声令下,收割真正开始了!一个季节的风风雨雨,播种,拔秧,插秧,除草,施肥,灭虫,灌溉……每一个环节,每一次的付出,就是为着这一刻的收获!
那一年,我读完中学,成了回乡青年。不久,就到了秋收季节。一天,队长对我说,今天跟我去粜粮。粜粮,就是摇船把队里的稻谷卖到公社粮管所。
那是一件美差呐!早就听说了,生产队里的男人们最心心念念的事就是能被派粜粮去。当然,队长只会派出工肯出力的男人去,是一种“奖励”呢。
当年,队里收上来的稻谷,绝大部分是要卖到公社粮管所去的。而那时队里的交通工具只有一条木船。记得这条船是七吨船,即可以装七吨稻谷。
为什么队里的男人都想去粜粮呢?原来,公社的粮管所就在县城。如果轮到粜粮,不仅有补贴,而且还有机会进县城里看看,更重要的是粜完粮后,还能去酒店里吃一餐。那时候,住在农村的人,哪有机会到县城下馆子啊。
每一个被派到去粜粮的人都喜出望外,干起活来便浑身是劲。那天,我们八个人,用簸箩将仓库里的稻谷一簸箩一簸箩地肩运到船,脚下生风,一路小跑,很快就装满了一船。顾不上洗去身上的淋漓大汗,乘着小河里的潮水涨满,就起锚出发了。
其时,天已近黄昏,天气晴好,风平浪静,夕阳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我们摇着粮船,离开生产队的小河,摇进了通往公社粮管所的横辽泾。我是八个男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队长掌舵,我摇舵绳。装满了稻谷的船,在船橹的一摇一摆中在河面上稳稳地负重前行。一路上,我们又说又笑,笑声从船上飞出来,掠过河面,一直飞到岸上;而说得最多的,便是对即将来临的那一顿晚餐的种种构想……
其实那一顿晚餐并不奢侈,菜是家常菜,酒是普通酒,但因为它是粜粮时的一顿特别聚餐,便成了难忘的记忆。既是对辛苦了一季的自己的直接犒劳,也是对丰收的一种特别庆祝,更是丰收之后喜悦心情的朴素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