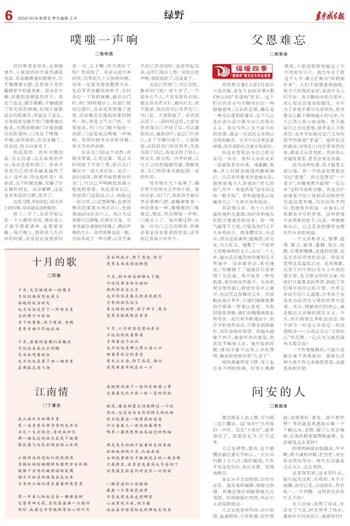□高明昌
回村看望老母亲,走到场地外,小妹家的阳光房里满是亮堂,母亲微微地仰着脖子,右手微撑着右腮,在那张古老的藤椅里半仰着身体。母亲在午睡,好像很是惬意的样子。我走了进去,蹑手蹑脚,手触碰到了阳光房的玻璃,拉到人能够进去的距离后,我就走了进去,反身将原先敞开的门慢慢地拉拢来,当两扇玻璃门合拢到最后的距离时,门发出了噗嗤一声响,虽然很轻,但母亲醒了。母亲说,你又回家来了。
我说是的。我所不懂的是:这么轻盈,这么短促的声音,母亲还是听到了。母亲不是说自己的耳朵越来越背了么?这声音,你也能听见?母亲说,这个时候安静,安静了什么都听得见。母亲解释,这是老早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这是习惯,我很相信,因为我小的时候,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我十二岁了,母亲开始让我一个人睡西房间,理由是儿子读书需要清净,也需要安静。每天晚上,到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母亲会在客堂里问我一句,儿子啊,你书读好了吗?我说快了。母亲从此不再问我,但等到九十点钟的时候,母亲一定前来替我整理书本,然后看看我睡觉的样子,有时会拉一下我的被褥,最后出门时,将门轻轻地拉上,拉到门框的位置时,母亲突然放慢了速度,母亲像是在提起很重的物件一样,用足力气关门的。尽管如此,当门与门框合拢的一刹那,门还是发出噗嗤一声响的。我那时暗笑母亲的顶真,我又不怕声音的。
母亲关门的这个动作,我眼里看着,心里记着。我认为时间到了半夜三更,轻点关门确实对一家人有好处。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便开始想着如何关门,可以让声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事情。我还没有忘记,我曾在门边的沿口上,粘贴过一层白纸,以此想降噪;也曾用棉花的絮絮头夹在沿口,也将菜油涂抹在沿口上。我以为这些都可以降噪,但事实不是。后来我就在速度的快慢上,测试声响的大小。虽然效果也是一般,但却养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离开自己的房间时,也曾竖起耳朵,去听门被合上那一刻发出的声响,到底是轻了,还是重了。
关自己的家门,可以实验,集体的门呢?读大学了,一个宿舍五个人,大家见我有点闲,建议我负责关灯,就叫灯长,我不愿意,我说我可以负责关门,叫门长。大家同意了。在我的示范下,一段时间过后,大家突然发现关门声轻了后,可以避免惊动,避免惊吓,也让门外的人,有了平静与安宁。大家悟觉,这轻轻关门好处很多,先是关照了自己,再是关照了别人,很文化,很文明。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传递,理解宽容,关门的轻重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母亲现在九十高寿了,确实禁不住咣当之声的干扰。每次回家,关门了,我的双手就自然会紧握门把,就像握着某一种的使命一样,慢慢地向门框靠近,靠近,然后噗嗤一声响,门就关上了。每次都这样,而每一次关门之后的转身,我都会看见母亲慈祥的笑容,这笑容让我高兴好多天。